2025年9月29日下午,由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办的“品读”系列讲座第四季·中国艺术经典第二讲在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(燕南园56号)举行。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欧阳霄主讲、山西大学哲学学院讲师陈静仪主持。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朱效民、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宁晓萌出席本次讲座并参与讨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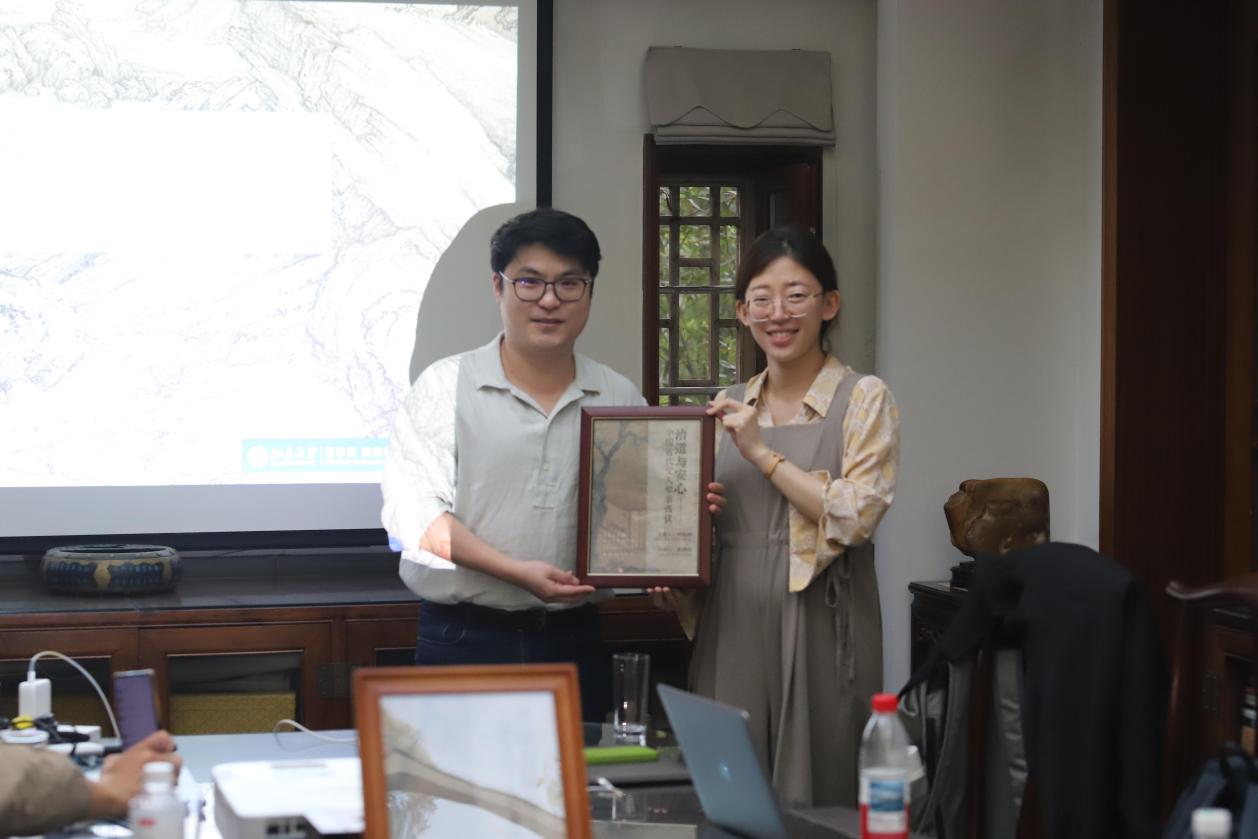
本次讲座的主题为:“治道与安心——中国古代文人琴事刍议”,主要从与文人的三种身份角色相关的琴事出发,结合传世古琴实物及诗文记载等,厘清琴之于中国古代文人在“治道”与“安心”层面的多重意义,同时亦探讨琴在文人生活世界中,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独特价值。
在引言部分,欧阳霄老师开门见山地提出核心问题: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弹琴?琴之于他们的意义若何?后续内容都围绕此问题展开。他回顾了自己在《重思高罗佩与文人琴传统怀疑论》中的路径,即结合文人画的平行案例,归纳文人艺术的一般特征,进而延展到文人琴上,讨论文人琴的一些规范性特质——比如以琴乐“自况”“自适”的诉求,对“表演心态”的排斥,致力于超越具体音乐形式而在音乐实践中涵养性情、探索更为深刻的体验与意义的旨趣。他指出这一路径的局限性,文人琴有其特殊性,不可和其他艺术门类简单通约,因而不能完全套用文人画的研究范式。本讲尝试对文人琴展开更为描述性的分析讨论。接着,欧阳霄老师以“九霄环佩”、“松石间意”、“飞瀑连珠”等琴为案例,展示了“琴铭”这一实物材料对于古琴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。在接下来的主体部分,欧阳霄老师从中国古代文人所具有的三种典型的身份角色——诗人、哲人、大夫出发,探讨与之相关的文人琴事。

在“诗人之琴”中,司马相如、白居易、范仲淹等人的琴事展现了琴在诗人生活中的多重面向。司马相如“将琴代语兮,聊写衷肠”,以琴传情,琴挑文君;范仲淹则“弦上万古意,樽中千日醇”,耽琴嗜酒,以美生平。白居易的琴事贯穿其人生各个阶段,从“琴诗酒伴”到“琴酒以送老”,琴既是他闲居生活中的良伴,用以陶写时光,更是其安顿生命、坚守独立人格的精神寄托。欧阳霄老师结合其琴诗进一步分析,指出其中既有“古声澹无味,不称今人情”的去俗之志,也有“自弄还自罢,亦不要人听”的自适之趣,更有“众耳喜郑卫,琴亦不改声”的守贞之节。欧阳霄老师认为,诗人之琴中最极致的一种体现是“琴痴”。在诗人琴事中,还强调不可忽略女性琴人的活动,提到李清照琴铭的相关轶事,特别分享了《瘗琴铭》中庄清卿与琴“性命相依”的故事,可谓“琴痴”典范。
在“哲人之琴”中,朱熹、陈献章、王夫之等人将琴从技艺层面提升至哲学思辨与心性涵养的高度,使其成为贯通天道与人心的重要媒介。欧阳霄老师重点剖析了朱熹的琴学思想。“太古遗音琴”刻有其《紫阳琴铭》一则:“养君中和之正性,禁尔忿欲之邪心;乾坤无言物有则,我独与子钩其深。”这是对传统“禁邪说”与“理性说”的综合,超出了传统琴学主张,把琴乐实践内化为理学家一以贯之的格物(穷理)功夫。此外,朱熹为刘屏山复斋琴所题铭文“主静观复修厥身兮”,进一步将琴与“主静观复”的工夫论相联结,展现出琴在理学家生命实践中的深远意义。
在“大夫之琴”中,孔子及其弟子、周必大、文天祥等人将琴与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家国责任紧密相连,使琴成为承载“治道”理念与精神气节的重要载体。孔门素有“弦歌不绝”的传统,孔子与子路“造次颠沛不舍弦歌”,展现出基于对自身使命与天命的深刻理解,不为外在境遇所动摇的精神定力;周必大撰《冯轸元方琴铭》末句“大则歌《南风》,小即治单父,举不出于斯焉”,化用舜歌《南风》和宓子贱“鸣琴而治”的典故,将琴的意义从个人修身扩展至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;文天祥于宋末危难中仍携琴谱曲、以琴明志,琴成为其在乱世中坚守气节的精神依凭。欧阳霄老师同时还援引《乐记》、《史记》的文本,探讨了“音乐与治道”的主题。

最后,在结论部分,欧阳霄老师对本讲内容进行总结升华。本讲以古代文人的三种身份角色为线索,通过相关的琴事典故,结合传世古琴实物与诗文记载,探讨了古琴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双重意义:既是参与“治道”(国家治理)的媒介,也是“安心”(安顿心灵)的方式。无论是以琴喻政的和之箴言,还是先王之治的符号代言(或者天人感应之依凭),琴可承载家国情怀、政治理想,是一种集体的文化意象和价值载体;同时,无论是燕闲之日的娱乐吟咏,还是困厄之时的生命高歌,琴与文人达成文化与生命的共生,文人左琴右书、耽琴嗜酒、琴剑相随甚至“性命相依”。此外,本讲也讨论了古琴在文人的艺术生活中,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独特价值,即其始终保持了家国理想与“以美生平”两种意义维度的共存,随着文人穷达、出处的语境不同而或隐或显。虽然在历史演进中,琴乐实践的“私人”化、“娱乐”化的诉求(“以琴自娱”)不断发展,乃至于成为文人琴事的核心特质之一,但文人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念在作为古乐图腾的“琴”的相关活动中一直被保留与滋养。琴之于文人的意义,在于上述个人体验与宏大叙事两个层面,这两个层面在不同人或者在同一人的不同生命时期是不一样的,但始终存在于“琴”中,不太可能全然分离。
在评议环节中,陈静仪老师高度称赞此次讲座“有材料、有学问、有情感”,她指出,讲座的材料运用极为丰富,除基本文献外,诗歌、实物材料(尤其是琴铭)构成了重要的文献补充;在理学与琴事的关系研究上颇有创见,引导大家对平日里关注较少的内容有了更多思考。

宁晓萌老师同样肯定了材料的丰富性并进行追问:其一,参照文人画以“职业化”为明确对立面的情况,“文人琴”是否具有清晰的对立传统?其二,在研究方法层面,她提醒琴铭可能存在“墓志铭”式美化或套路化表述,研究中应如何看待其可信度?欧阳霄老师肯定了问题的启发性并回应道,其一,讲座所使用的“文人”概念的确非常宽泛。文人琴并未形成如文人画般鲜明的对立传统,一方面根源在于前面讨论的琴自身的特性与历史,另一方面,文人通过一系列的论争(如雅正之辨、时古之辨、夷夏之辨)凸显琴的特质,进而巩固 “文人”对琴的“垄断”地位或文化共生。其二,针对琴铭材料可信性的问题,他承认现存琴铭确实常有“伪作”现象。但即便托名之作,仍基于对琴之真实意义的理解,而从某些作伪意图中恰恰反映出特定群体所崇尚的价值观念。

朱效民老师也从自身对文人琴、文人画的体验出发,对两者在意境上的同异进行了评议。同时他结合自身修习太极拳的经验,在“白居易是否能琴”的问题上提出见解。他认为白居易堪称“诗人之琴”的典范,即便白居易常弹仅《秋思》一曲,在技巧上未必繁复,但如同太极拳那般,抚琴的核心价值不在动作或技巧的多寡,而在于过程中蕴含的意趣,从这一维度来看,白居易的抚琴水准实则颇高。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落下帷幕。

纪要整理:李林熙
讲座摄影:马彦茹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