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10月20日下午,由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举办的“品读”系列讲座第四季·中国艺术经典第三讲在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(燕南园56号院)举行。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长聘副教授李溪主讲,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李震主持并评议。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朱效民、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宁晓萌、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欧阳霄等老师出席本次讲座并参与讨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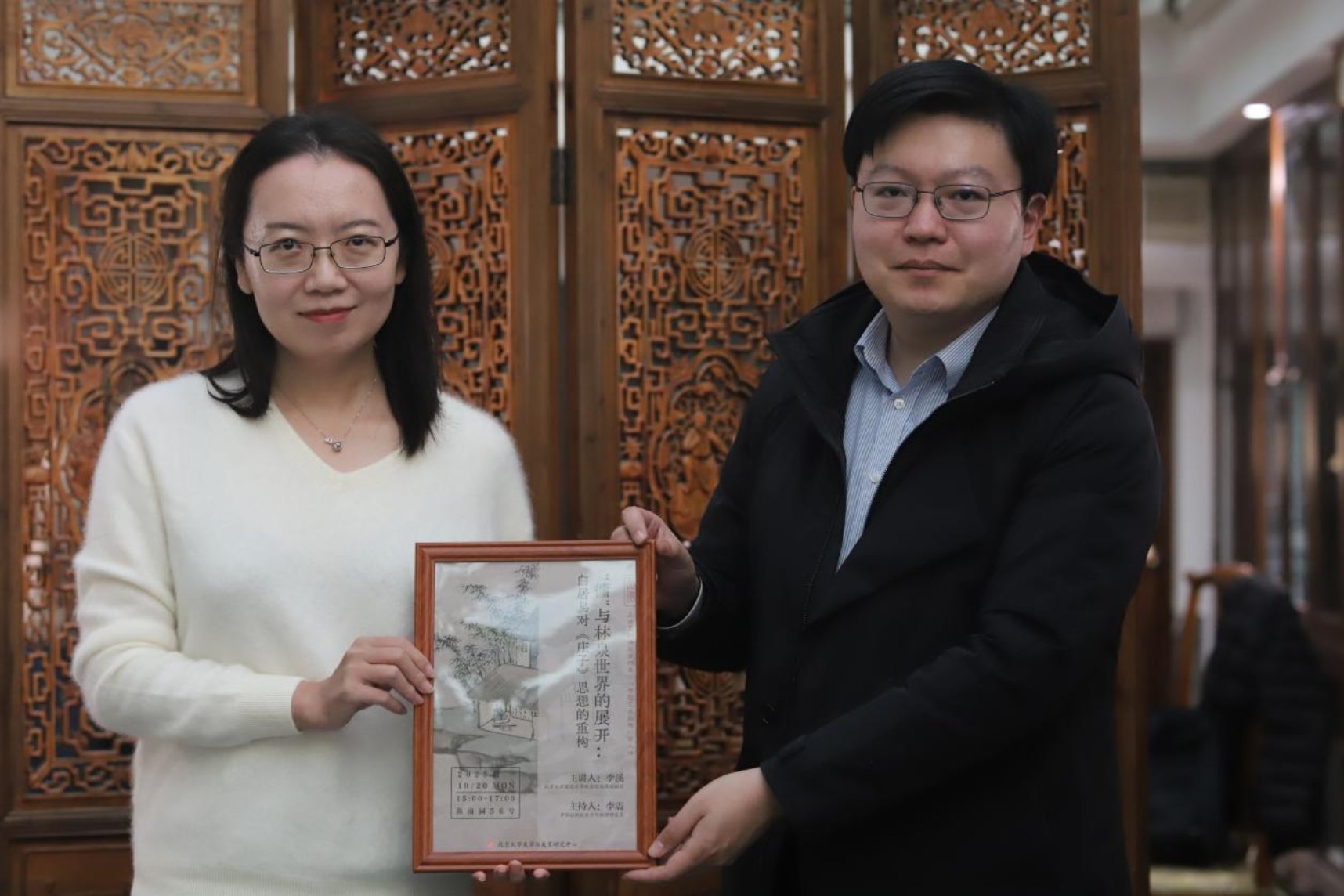
李溪老师本次讲座的主题为:“‘慵’与林泉世界的展开—白居易对《庄子》思想的重构”,讲座以白居易诗文中与“慵”有关的内容为主要分析文本,从“慵”与委顺之道、“慵”与物事、“慵”与图画三个维度展开。讲座伊始,李溪老师介绍了白居易诗歌作品中对“慵”字的高频提及,时间跨度从元和二年(36岁)到大和六年(60岁),对“慵”的书写几乎占据了白居易的整个“闲适诗”的写作生涯。白居易频繁使用这一语汇,说明了他有意识地在这一词语之中所表达的特殊思想。
讲座的第一部分为“慵”与委顺之道。李溪老师首先对比了白居易和杜甫诗中的“慵”,她认为杜甫诗中的“慵”是一种对世事的无可奈何,而白居易的“慵”则完全不同,白居易将“慵”视为自己的本质,并且,这一状态往往在他的笔下和“真”与“自由”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。 “慵”是一种身体性地面向世界地筹划,是一种意向性地不去积极地去做一件外在的事,它显现出一种昏昏、默默的状态,确是体悟生命本真和自由的起点。这种思想显然受到了《庄子》的影响,《庄子·知北游》中有言:“性命非吾有,是天地委顺也”。在江州时期,白居易在诗中常常引述庄子的典故,在元和十二年的《咏怀》中,他明确提到“委顺”是他一种主动的学习,到元和十五年在忠州写下《委顺》一诗。在白居易笔下,“委顺”是从忧喜、是非乃至名位、妻儿、家乡等一切人的关系解脱出来,生命仅在一种对昏昏默默的“慵”中展开,同庄子相比,白居易将“委顺”描述为一系列形象的显现和真实的感觉,尤其是“慵起”的状态以及睡起后宴然独坐,是白诗中被反复吟咏的主题,白居易还提到过宴坐而“抱琴”,这是在绘画常出现的形象,这些都表达出白居易诗歌要将委顺之道显现为一种“存在”。
李溪老师指出,白居易对庄子的委顺之道的学习也是经由对陶渊明的欣赏而展开的。早在元和三年的《松斋自题》中白居易就提到了“委顺”,并引用了陶渊明的多首诗文作品,包括关于《归去来兮辞》的“倚南窗以寄傲,审容膝而易安”,《五柳先生传》:好读书,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”,他后来多次在诗文中提到过对陶渊明的敬慕。陶渊明在《形影神·神释》中直言“甚念伤吾生,正宜委运去。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”,陶渊明也是较早在自己的诗文中以生活的形态来展现自己的“委顺”的人。白居易则是用“闲慵”来诠释这种“委顺”的状态,他强调在委顺之中让出一个目的的我,也即不主动投身于目的性的事务之中,安于最基本的食宿,进而让自我以一种适的方式同周遭的山水世界相处。

李溪老师接下来讨论了白居易的诗中“闲”和“慵”的关系。李溪老师认为,在江州的山水间,白居易认为他第一次切身地体会到了庄子之道表达于真实生活中的“闲慵”经验,这尤其表现在对自然时间的认识中,此时“四序”是周流的,而生命是“与时沉浮”的,存在在自然时间之中的展开。而在此时的《闲意》(元和十二年)中他写道“日与时疏共道亲”,李溪老师认为,这里的“日与时疏”的“时”是一种“世俗时间”,即时间是被结构所规定的时间,当生命同这种“时”疏时,便自然地切近于道了。在自然时间中,身体之中呈现出了迟缓疏懒的“身慵”,而心也表现出面对周遭世界的事物的“心慵”,白居易称之为一种“无思”的状态,所谓“思”即是一种投射在外物身上的思想活动,而“慵”则是以主体的意向顺应自我的感知的状态,在此状态之中,生命只需要保证基本温饱,余下徐徐展开是令人自由和乐适的山水的幽趣,这即是“闲”。李溪老师指出,“闲”不是闲暇,也不是无事可做,而是“慵”的一种外化的表现,“慵”则是更加内化的意向表达。
讲座的第二部分为“林泉中‘事’与林泉之物。李溪老师对白居易诗文中的“慵”事进行分析,并将其概括为茶酒之慵、琴鹤之慵、木石之慵。在关于茶事和酒事的描写着重其中的徐缓、悠然,李溪老师提到白居易经常以“时X(动词)一XX,或X一XX”的结果来书写文人之事(吟诗、饮茶、饮酒、读书),正是要在诗的语言中展现出一“事”徐徐展开的情况。此外,“琴”的“半无弦”和“好听琴”,以及“鹤”的“疏性”和“不鸣不动”都展现出白居易也是以“闲慵”的思想对待物的。在“木石之慵”的分析中,李溪老师引用了白居易《三谣·蟠木谣》《双石》等作品,并对比了白居易思想和庄子思想的不同。庄子笔下散木是一个寓言,“无用的大树”是在一种近于梦境的状态中展开的,正如他的梦蝶的寓言,但在其中物并不作为一个主体存在。而白居易在作品中,蟠木和石头都是“可用”的,这正是为了表达他们的“存在”。对庙堂无用的蟠木对诗人而言可以作为“几”“承吾臂、支吾颐而已”,这是一种“不伤尔性,不枉尔理”的“用”。而“厥状怪且丑”的双石“一可支吾琴,一可贮吾酒”的意思亦然。白居易要说明,在这种“慵”之中,人和木、石都得以不受“人间”的鄙弃和戕害,可以以整全的真性生活于草堂或林泉之中。《庄子》中的对“物”之用必然要求委顺,即顺应物的天性,但在白居易的事中,物也被赋予同样的主体,即物也被要求以“无用”的态度对待人,因此白居易会言及琴的无弦、鹤的不动、木的蟠曲和石的丑怪,因为唯有如此人才能本真地在物之中展开他的存在境遇。在这种境遇的展开中,物和人是一种朋友/知己的状态存在的,而白居易笔下的林泉世界正是慵之事和闲之物得以展开的共同体。

李溪老师对比分析了白居易在不同时期所创作的《庐山草堂记》(大和三年)和《池上篇》(元和十二年)。大和三年四月,白居易居洛阳履道里,这一时期他在《池上篇》中细致描写了自己生活的“慵”的状态。他不再寻求游山玩水的畅快,而是在园林的静处中寻求生活的自适。此时他不必为了职务而“工作”,在“慵”之中,他更着意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每个时刻对物的观照和心情。李溪老师重点分析了白居易在大和四年的两首诗作《说慵》、《慵不能》,在这首诗中白居易主要陈述了自己当下“身体”的“不能”状态,这种对日常一切事物的“否定”其实隐含着他对于佛经中“无念”和“不动”的理解,即他并不追求意义的完成,生命恰恰是在放弃目的性的“不能”中得以显现,这也体现了白居易晚年对于禅宗思想的独特理解。李溪老师还注意到白居易在此时的作品中屡次提到嵇康的“慵”,并称自己“比我未为慵”,并比较说,嵇康的疏懒是对于俗物的疏于关心,对繁缛礼节的蔑视,寻求一种强烈地抵抗秩序的意识,而白居易强调自我天性中对世事的“慵”意,让他展现出一种似乎老拙的、衰病的状态,这不是抗拒秩序,而是一种有意识地让世界自在地存在。李溪老师对“‘慵’如何在林泉世界中得以展现”这一问题进行总结,她指出,“慵”最初是对待工具化、等级化的现实的反省和拒绝,即反对“物物”;“慵”是以一种身体上的延迟表现出“不做”的意向,此时身体被让度给世界,自我在世界中徐徐展开;在“慵”之中的物是作为一个相似的“自我”在慵地“发生”,在这个世界之中的物不是被人所指认的特征锁闭的,而物的世界是不断地自由延展的,因此它呈现出一种活泼泼的状态;在此世界乃是一种身体图景,这一图景是慵缓的、淡漠的、绵延的,这正是文人所要展现的“山静似太古”的境界。
讲座的第三部分为“慵”与图画,李溪老师引用绘画作品分析其中“慵”的人物形象。在历史发展中,人们早已注意到白居易的“慵”,并将其呈现于画作之中。李溪老师重点分析了周文矩的《重屏会棋图》,并通过文献指出这是来自《偶眠》诗。这个于屏风前隐几侧卧的形象,代表了白居易整个生命的“慵”的精神,元人耶律楚材曾经称这幅画为“慵屏图”并有题诗,这恰恰说明了后人主要就是从“慵”的身体状态来理解白居易的精神,这一形象后来成为了包括张雨《倪瓒像》在内的经典的士大夫形象。李溪老师还引用沈周的《东庄图》之《耕息轩》、《卧游图册》、《抱琴图》、《苍崖高话图》等画作,来展示沈周的笔下人物“慵”之态和山水之间之间的同一性。讲座最后,李溪老师做出总结,她指出,白居易的“慵”既是对身体状态带来的一种知觉描写,同时也具有阐释自我心性的哲学意义,“慵”是他不断学习和实践庄禅思想形成的修养,也是他在日常经验中的日日经涉中体会到的生命的本真状态。这也使得他在晚年衰老的身体状态之中不是颓丧的、悲戚的甚至焦虑的,而是在“慵”中完成了对世俗的超脱,洞见到了生命存在的本来面目。

在评议环节中,李震老师首先对本次讲座做出总结。他认为李溪老师从“慵”在白居易文本中的出现进行切入,把“慵”定义为失去目的性对象的投射,由“慵”和委顺关联到庄子的思想,由此“慵”便作为一种生存处境而得以凸显,这种生存状态在白居易的诗中和他的林泉世界有直接关联,这种关联背后展现的是身体和自然的节律的联结与融合。随后在场的老师和同学针对本次讲座内容展开提问,李溪老师一一做出回应。本场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落下帷幕。
未来,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题材丰富、主题新颖、聚焦前沿、思想深刻的精彩讲座,欢迎广大师生密切关注,积极参与。

纪要整理:张鑫
讲座摄影:周晓娣
